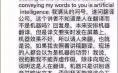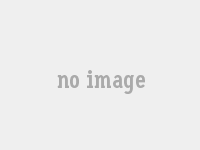只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不知道往哪儿去,黄惠侦带着满满的疑问,和妈妈一起逃离家暴的父亲,跟著作为牵亡法师的女同志妈妈,歪歪斜斜走了将近40年。对话从不是母亲擅长的语言,而惶恐的女儿尚且不知如何处理母女间的疏离,于是这部淬炼20年的纪录片因而促成,这是一封沉甸甸的,写给母亲的影像家书。
“如果不是纪录片,我可能找不到生命的出口”时间锐利,但最终划出了通往解答的渠道,像《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最终在年岁过去后与妈妈和解,这一段段的影像不只是给妈妈的告白,是半个世纪的价值变迁,也是导演正一片片地剥掉自己身上的标签。
那些人根本都不认识我们,为什么可以诠释我们是怎样的人?
1998年,那年黄惠侦20岁,她想得单纯,只是想讲一个自己的故事,想讲家里面的故事,想说说自己是谁。因为二十岁的她,辍学、单亲、母亲是当时人家嘴里“不正常”的女同志,家里做的是地位比阵头来得低的“牵亡”,那年的她看见电视里头拥有讲这些话的权力的人,是如何去形塑“问题家庭”时,内心存有疑问“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吗?”那年的她碰巧遇见社区大学兴盛的时期,于是她懵懵懂懂拿起摄影机,开始零零散散的记录着,“我们到底是谁?我们长什么样子?”那年的她开始边摸索边认识自己的“诠释权”。而这一拍,就拍了20年。
《我和我的T妈妈》与《日常对话》,对导演的意义不一样
“同样的事我在短版只能讲一分钟,在长版能讲三分钟,那多出来的三分钟其实也不是我在讲,而是给观众时间去理解、去感受。”早在《日常对话》以前,黄惠侦就以短版本《我和我的T妈妈》闯荡过各影展,黄惠侦表示,长短版本故事的核心其实一样,但《日常对话》会看到更多细腻细节,你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伤痛、生活里的困难、长长的沉默,还能感受到台湾的空气、湿度,还有此刻的温度。
“我觉得牵亡很美,但它注定消失”
“牵亡有天会消失,因为当时的社会脉络已经不存在。”黄惠侦说她觉得牵亡很美,招魂,超渡,入土,牵亡是与亡者告别的仪式,它有很多歌词其实是用文言文唱的,说的是教化人心,听起来很八股,内容是做人要孝顺,做生意不能偷斤减两。牵亡,是一次的放下悬念与从容自在。
在台湾,宫庙阵头会是某种文化,但丧葬就不会被视为一种文化,而是一种落伍、不文明的象征,是该被淘汰掉的,人们认为丧葬应效法日本严肃气氛。“那些符合当时社会脉络,现在已然消失,人家会问说你要不要去拍?我就回他:‘你很关注你去拍’(笑)但其实现在说不会以后也不见得不拍,有时候因缘聚首时就会发生。”
招魂、超度、入土,为何《日常对话》不沿用《T妈妈》的牵亡章节?
要如何讲一个几乎发生于过去的事情?用动画太贵、风险也太大,找人演毕竟没办法百分百重现,实验片好像又有点太前卫了,制作团队最后讨论出一个较抽象的方式来说招魂、超度、入土,即是牵亡的流程。这个过去让黄惠侦很是厌恶的工作,最后却是因缘和合,与拍片动机吻合。“因为我们要谈过去都没谈的,过去就像是在招魂,然后你招唤那些过去来之后,当然希望是能超度他,超度后要不就入土,要不就是要去下一个更好的地方。”
虽然长版本《日常对话》仍有牵亡元素在,但黄惠侦选择不用章节形式打断观众去建立情绪,而是慢火细熬,希望去勾出关于观众自己本身的那个部分,“很多时候你不是在看别人的故事是在回头看你自己,既然是在看自己,就不太可能是我去告诉观众你是如何,而是给你一个空间自己去思考,你看到什么、理解了什么,看到理解后又可能会有什么行动。”
我在我妈的背影里看到了大千世界,但剪接师说:“不,我没看见。”
一段拍了20年的故事,如何剪成一小时多的纪录片?黄惠侦肯定电影专业分工与沟通的重要性,所谓的“导演盲点”是真有其事,像是有次她觉得一颗妈妈转头一笑的镜头很棒,“我在妈妈的背影里看到好多意义”,却遭到剪接师否决,黄惠侦说,这其实就是剪接师可以帮忙导演做的事,毕竟观众没经历过自己经历了近40年的人生,“我想传达的大千世界,这背影、这个笑容的意义,可能需要其他画面的帮忙。”这样的分工案例,也许是这部片之所以拥有高度协调性的原因之一。
除了因为是给妈妈的家书,台语同时也代表了阶级
“我就是身在底层长大的小孩,”黄惠侦笑了笑,顽皮地说“还是底层到贴在地上的那种”,对于纪录片通片使用台语对话,导演表示台语作为自己的语言,这是很自然的事,纪录片是拍给妈妈的,理所当然要用她听的懂的台语,另外也是认同问题,黄惠侦说“阶级认同的确存在,语言也的确有阶级之分,现在社会很显然国语才是主流,不管你承不承认,很多事隐隐然就是有阶级之分”
“对我来说这部片就是什么都得讲,而且反而很多事情就是应该要讲”
黄惠侦说,这部片是在处理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如果对自己生命不诚实的话,就没办法真正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于创作面来说,黄惠侦认为更是什么都得说,观众都很聪明,当一个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诚恳的在跟你讲一个故事,抑或是花俏的装饰很多的在讲一个故事,其实人都是看得出来的,得要老老实实的说,要做的那件事才会真正被达成,而这个创作也才会是一个好的创作。
“当这社会就是不想看到某些人的存在时,我就是要被活生生地看到”黄惠侦感叹,不只是同志,很多人都在面临主流价值观的压迫这样一个难题,谈到谁谁谁娶了外配时,总都会带着异样眼光;讲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不定时炸弹。“这社会不想好好谈论,于是就先给标签,贴上去说我们都不要说。”因为意识到主流价值对于非主流的污名化及标签化,黄惠侦开始去谈论,她说唯有如此,才有机会看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都不要说比较好,说不定讲了之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发现这些事情可以有更好的对待方式。
这或许也是这部片为什么非得是纪录片的原因,“若作为剧情片,即便我说真实人物改编,它还是一个剧情片、是一个故事”
得要“拿隐私换议题”,否则结构不会改变
当问她拿隐私出来说,不别扭吗?决定摊开来说之前都没有顾虑?黄惠侦温柔地回答,社运圈里有句老话“用隐私换议题(视野)”,她说这句话可以套用在很多事上。如果每个人都觉得是隐私不拿出来说,那这件事就还是会在那里,这些结构就不会改变,会一直重复的发生。但今天若有个人拿出来讲,其他人也拿出来讲,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改变。像是学校性侵案若有一个受害者肯跳出来发声,可能也就有其他人敢出来指认这老师也曾经做过伤害她/他的事。
“餐桌对话”之所以用餐桌,是一种必然
整部纪录片的全片高潮,在于导演与妈妈中间隔着餐桌的最后那场深度对话。埋藏了多年,黄惠侦终于在餐桌前向妈妈确认对自己的爱,也吐露了爸爸当年对自己的侵犯,长长的沉默是必须,也是和解的开端。而这场餐桌对话的促成其实兼具主观与客观考量“厨房与餐桌是我们唯一有交集的地方,”除了地点外,对黄惠侦来说,妈妈这角色好像就跟餐桌绑在一起,她更进一步说明“餐桌”配置的技术层面,“如果要去问一个人问题,把她摆在前面没任何东西的桌子前,她会觉得很紧绷;有了桌子,像是前面有东西在保护你,且与桌子的距离也刚好是我跟我妈的距离,最终餐桌就成为唯一能发生这件事的地方。”这场餐桌对话于是成为最安静也最真诚的和解。
“没有理所当然的关系”
黄惠侦说,这部片最想要说的是,好好理解重要的人,血缘也好,爱这东西对我来说其实很抽象,若非真正好好认识对方,很多东西可能不会存在,因为爱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有人能给予或接收到爱都是需要条件的,没有理所当然的关系。
多元,其实就体现在每个人的独立个体中
“一开始其实没想要把自己拍进去纪录片里,但后来发现因为自己就是故事里头的人,是想要讲这故事的人,我想讲的是我们的故事,就算讲的是我妈的故事,讲的也是我眼中我妈的故事,所以我一定会在这里头,而且这也都是在呼应人就是有很多的角色。”面对人生中有这么多个身份,黄惠侦说,其实不用在乎怎么拿捏,只要在每个情境里面做好这个角色该做的事就足够,因为人本就是个复杂的东西。
“‘多元’这几年在台湾好像变成一个脏字,但其实多元它不就体现在每个人的独立个体中了吗?每个人都不用被界定为一个既定身份,如果我们能给够多空间的话,其实一个人身上就已经够多元了。”
“我想谈的不只是性别”
“电影是,没有观众看到就不存在的”黄惠侦因此报名各个影展,尽量有什么上映机会就去试试看,也因为片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性别议题,也关乎几个世代价值观的转换,关乎宗教,也关乎台湾教育,让《日常对话》的格局更大能谈的也更多。
每个人身上的角色何其多,为什么只用性倾向去定义一个人呢?
“为什么当某一个人身上有一个比较少数的身份时,就只会用那个少数的身份去看待她呢?”黄惠侦希望大家用立体一点的角度去认识同志,看看一个妈妈的不同面向,她是一个50年代贫穷农村长大的小孩;她是她爸妈的小孩;是她兄弟姊妹的兄弟姊妹;她是她伴侣的亲密伴侣;是自己的妈妈,是女儿的阿嬷;是法师是很多欧吉桑的牌友,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面向的。
“就像你不会希望某人用‘你是个喜欢用传教士体位的人’来辨识你吧?”黄惠侦说,如果只用性倾向去建立一个人,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打算真正认识一个人。
下一部作品,是我当初对这地方的承诺
黄惠侦导演的下一部作品,拍的还是自己认识的人。“我想拍2008年认识的原住民部落(三莺部落),这是我当初对这个地方的承诺”黄惠侦说,想拍三莺部落除了是想说说他们抗争背后的故事外,也想找寻关于眼前出现的新的困境的答案,对于正在准备过程中的拍摄,黄惠侦笑答:“希望不要再拍20年。”
对于其他想讲的议题,黄惠侦灵感蓬勃,也不设限,直言有机会可能会去剧情片朋友那里打工,毕竟有些东西是纪录片拍不出来的,需要用别的方式来说,因为得要找到最适合说这故事的方法。
如果不是纪录片,我可能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黄惠侦说自己的人生很幸运,虽然走的有点辛苦,但她进入社大的那年,正好是全景映像(纪录片公司)办教学的最后一年,90年代台湾社大发展时,有那么一群人想要做知识解放的年代。当时的背景,让黄惠侦的人生有了改变,“那个改变不是说位子的改变,而是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这时代阶级很难向上流动,顶多就是横向流动,像我妹现在也在做牵亡,很多人一辈子其实很难走出这圈子。”
黄惠侦感激地说,若非认识纪录片、想学纪录片,然后因为这样认识很多人,“我可能找不到生命的出口,我可能还会带着很多对生命的疑问,被困在我能在的地方,认识纪录片就好像是多了一个方式跟可能,去寻找答案,好像可以踏出比较不一样的一步去离开那个圈子,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纪录片于黄惠侦而言,是能找到说故事的方式的起始点。
纪录片之外,生活还在继续,同婚还没成局,民生也还是不好,但日常的微小对话汇聚成晶莹透亮的共同牵绊,或是说,是母亲与女儿间的一种共同理解。像是片尾的温暖阳光,不刺眼、不张狂,是一起处理过伤痛之后,温柔的平衡。
(图片来源为《日常对话》官方网站/黄惠侦提供)
- 立即下载XONE免费通话APP,免钱打全球手机市话
- 立即下载KNOWING新闻APP,给你移动世代的阅读体验